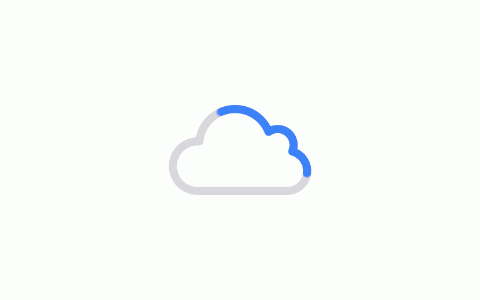幸福的童年疗愈一生。不幸的童年要一生来疗愈。
妈妈做的过年美味,足以幸福孩子的童年。
70年代农村孩子,大家都很穷,但孩子们往往都不缺乏幸福。
因为穷,孩子们的幸福基本都在吃上。那时候好吃的还真不少,黄窝子就是一道美味。
黄窝子就是松蘑,各地叫法不一样。夏、秋天在有松树的岭坡地生长,夏天的叫伏窝子,秋天的叫秋窝子。天气太热的酷暑三伏天反而没有。
在一个初秋晴热的午后,我娘从很远的山坡捡拾了一担黄窝子回来,沉甸甸两篓子,压的我娘头发汗湿的一缕一缕的,褂子背面都湿透了。我们赶紧把黄窝子倒在铺着平整石头的天井里晾晒。在晒热的石头上,黄窝子一下午就半干了。夏天天很长,天一擦黑,我们就在天井里摆上长桌,三个姐姐和我,还有爹娘,一家六口,坐在小凳子上吃晚饭。夏日里晚饭的美味是蒜泥拌黄瓜和炒芸豆,都是自己菜畦子摘来的。吃过晚饭撤了桌子我们就铺下我配合爹打的草席乘凉。仰面看天上的银河,找牛郎星、织女星和北斗七星。我娘和大姐在半明不黑的夜里掐辫子(一种用麦秸编制的一指宽的草编,能卖钱的)。细麦秸在水里泡了大半天,软了好掐。在手里上下翻动的麦秸杆偶尔会甩出细水滴,洒在我脸上。不知啥时候我就睡着了。
第二天再有一个好日头,黄窝子就晒干了,皱皱巴巴的。
孩子们的日子总是漫长。不知过了多久,就到了新年。那不知随便放在哪里的黄窝子出来了,大年初二上了我们的饭桌。那时候只有大年初二的中午,才是我们全家大吃一顿的好时候,就像一年的辛劳、积攒和愿望和等待,在这一天发力。我爹亲自打的鸡冻、猪冻,还有黄窝子拌白菜丝,豆腐贤子拌菠菜,猪肉炒白菜,就足以撑起一桌美味,都是我们最爱吃的。
我娘把黄窝子用水泡软,仔仔细细撸掉沾在上面的草叶和泥沙,洗得干干净净,湿滑柔软。裹上面粉,放锅里一煎,煎成半软不焦,貌不惊人的样子。然后切开一棵大白菜,抠出菜心,切丝,用蒜泥、盐,醋,加入煎好的黄窝子,美味就成了。要知此事须躬行,你不亲自尝尝,我根本没有词语来描述有多好吃。
长大以后来到异乡城里过人生,好久没吃这道美味了。这几年大姐发现了居住的县城边上山坡有黄窝子,很是高兴,连续几年都去捡拾,乐此不疲。然后挑最好的给我送来一袋子。黄窝子拌白菜又回到了过年饭桌,只是不再是当年一大家子人了,姐姐们各自有家,父亲故去已久。现在是我动手制作,儿子捣蒜,我娘不用动手了。老婆和儿子都喜欢吃。我觉得她娘俩吃的味道,肯定比不上我和娘吃得深有滋味。
有一次我把这个美食带到了朋友的聚餐会,大家都很喜爱,问我做法,我详细告之。
朋友们吃到了我们故乡的美食。
我吃的,是故乡的味道。故乡是平度东北山。
最后补充的是,胶东的大白菜,也是灵魂的伴侣。
本文来自投稿,不代表展天博客立场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me900.com/277177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