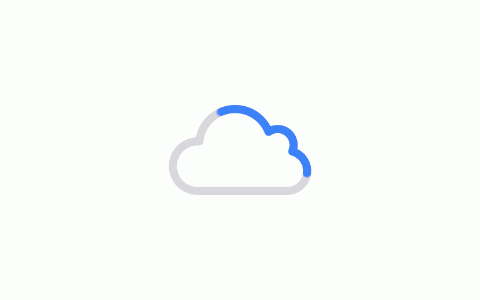“搞”是什么意思,你真的懂了吗?
要说能文能武,亦正亦邪,雅俗共赏,最重要是神通广大,一举就能铺开中国人说话版图的一个动词,一定是“搞”。这个魔性的发音——gǎo,我们中国人最懂。
“搞”是个伟大的汉字,这个自带魔力的字用途广泛,上至庙堂下至江湖,它无处不在又无所不能,它是触及灵魂深处的尖刀,又是拷问道德的重锤。
搞字有时候是滑稽的,它可能是搞笑,可能是搞怪,也可能恶搞。
搞字有时还会非常励志,任何需要想方设法进步提升的领域,都可以“搞”。
去年口碑一塌糊涂的《爱情公寓》电影,曾用名“终于,又双叒叕回来搞事情了”。
股市搞一搞,搞不好可以关;新闻可以搞一搞,但不要乱搞瞎搞;咱们要想个办法把KPI给搞上去。
生活里更离不开搞,无论是搞钱还是搞锤子,我们千万不能搞错,不然这事真没法搞了,万一被你搞砸了,还得我来帮你擦屁股。当然,没有我搞不掂的事。
搞字还时常被用到男女关系之中,以前我们管拍拖、谈恋爱叫搞对象。但搞字的下流气质也是掩饰不住的,在王小波,破鞋是不能乱搞的。乱搞,是对人的道德品质深层次的拷问。
“搞”字可以很老干部,也可以很儿女情长。语言学家也许会辩驳,你们什么都用“搞”未免太粗俗,太匮乏。但“搞”也很酷,翻天覆地,百无禁忌。
“搞”,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
“搞”字,在《康熙字典》里异形同“敲”,同“靠”。按照《说文解字》里的解释,它是从“搅”字分化出来的,其本义是“搅,乱也”,后来才引申出了其他意义。
关于“搞”字怎么来的,不少说法是来源于抗战时期,剧作家夏衍在广西桂林主编《救亡日报》时首创了“搞”和“垮”这两个字。
更有学者考证,“搞”字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。比如西汉贾谊的《过秦论》里有一句“执搞扑而鞭笞天下”,不过当时注释是将它视为“敲”的异体字,即“短杖”之意,意义上与如今的搞,是风马牛不相及的。

搞飞机,意即捣乱、惹麻烦。
到了现代汉语,“搞”字逐渐脱颖而出,几乎可以说包罗万象。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,对动词“搞”的意思有几种解释:1.做;干;从事;2.设法获得;弄;3.整治人,使……吃苦。也就是把动词“整”“弄”“干”都包揽了。
然而同样是万能动词,“搞”的概念意义非常丰富和复杂,慢慢从一个没有感情的动词演变成带着方言、语体、感情色彩的词语,可以延伸的意义,绝对不止以上三种:
比如“搞个计划”。(拟订)“他这场病,把他身体搞坏了。”(使……变得)“你怎么搞得妈眼睛都红了。”(气得,惹得)“这对父子还真够难搞。”(对付)“这点他还是搞不过我。”(赶得上,比得上)“还要自己掏腰包搞饭吃。”(谋生)“那就不怕他搞鬼了”(暗算)……
通晓梵语、巴利语、吐火罗语等语言的季羡林老先生,对“搞”字也是服气的。
他的《谈国学》一书里说到,当时他从欧洲回国时,途径西贡和香港,从华侨和华人口中听到了“搞”和“伤脑筋”这个词,就让他非常伤脑筋:
“‘搞’是一个极有用的字,有点像英文的do,现在我们张嘴就搞这个,搞那个。”

电影《惊声尖笑》在香港在被翻译为“搞乜鬼夺命杂作”。
“搞”作为方言用词在现当代文学小说里,也在影响着作家的地域气质。南方作家写文章,“搞”就是北方作家使用的频率要高。
比如哈尔滨的作家迟子建8万字的小说,“搞”字就只出现过一次;湖北作家池莉笔下的武汉人,生活经常是“搞”来“搞”去的,15万字的小说里,“搞”就出现了45次。
其实具有广泛意义的动词,遍布大江南北——“搞、整、弄、干”四大动词几乎集中了所有汉语的精华。大东北爱用“整”字,华北地区“弄”字先行,南方多数用“搞”,东南一些地方特别爱用“干”。
这四个字在某些场合意义相近,“搞啥子”、“搞么春”、“整啥玩意”、“弄啥咧”、“干什么”,基本统一了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的疑问句。

电视剧《插翅难逃》(2002)。
“搞一下”、“整一下”、“弄一下”、“干一下”,成为了广普撩骚话术,虽然略显粗鄙,但这种朴素的情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并不违和。
总体而言,“整”更加正式,甚至是能上得了大台面的,比如由“整理”引申而来的“整风”,从来没人说搞风、弄风、干风;在职场经常有“整人”,但“弄人”通常会想到造物,变成人生的唏嘘;千万别变成“搞人”,瞬间会低俗不少;至于“干人”,特殊用法,语境不对。
粤语“搞风搞雨”必须连起来用,意即捣乱、折腾,与“整风”不是一个意思。图/电影《 我的失忆男友》

“搞”——现代人的百搭哲学
一说到“搞”,也许你眼前会不由自主浮现出五大三粗,穿着大码西服的油腻中年男领导形象,开会发言三句不离“搞”——
“小李啊,今年市场营收数据太差了,你这是乱搞啊,这个搞法不行啊,明年要朝这个方向搞一搞,把这个数据给搞起来。”
的确不是什么人都能用“搞”的。
看看“搞”这个形声字就知道了,提手旁加一个高字,高手才能“搞”起来。只有高手才能搞经济、搞国际贸易、搞里应外合、搞城市规划、搞文明建设……


“搞城市建築”。图为新加坡的组屋建筑。
老舍先生曾经在《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》一文里研究过“搞”的艺术用法:
“我写一个长辈,看到自己的一个晚辈有出息,当了干部回家来了,他拍着晚辈的肩说:小伙子‘搞’的不错呀!这个地方我就用‘搞’,若不相信,你试用‘做’,用‘干’,准保没有用 ‘搞’字恰当亲切。
口吻就跟长辈跟后辈,上级领导跟下属沟通方式一样。“搞”的万能不仅仅在于字义跨域地区,还能跨越阶层,用“搞”字恰到好处地缓和了代沟,又不失阶层等分。
现今我们年轻一代说“搞”,更多是消解这样的权力差距。“搞”从来就是官民皆用、雅俗共赏的口语动词。
尤其是到了当下,被人说“你很会搞”其实是一件好事,那代表着我们在行,被人说“你真的很搞”,同样也是一种流行褒奖,说明我们有趣,会玩。

“搞咩呀你?”(搞什么啊你?)
“搞”已经衍生成了一种小人物精神。尤其是“搞笑”和“恶搞”这两个从粤方言进化过来的词汇,由周星驰的无厘头香港电影发酵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内地年轻一代。
“搞”在粤语这片土地上更是野蛮生长起来。“搞乜鬼”“搞咩呀”(干什么)“搞掂晒”(搞完了)“有乜搞作”(有什么新主意)……这些带“搞”的方言组词听起来有些粗俗,比如“恶搞”“搞怪”就带着草根化的娱乐精神,用一种调侃现实,消解固化无聊的阶层权力。
我们爱用“搞”,不是恰好就用这种粗俗的语境,来调侃打破原有的官僚和形式主义吗?
“搞”对当下言语匮乏又懒惰的现代人,就是一种百搭哲学,什么都可以“搞”。毕竟也就只有“搞”字,才能带来可意会不可言传的“爽”感。
我们现在不单单说“搞”(gao),更衍生出新发音(giao),愈显模糊抽象的变种,就愈有点魔幻朋克的意味。
就像我们聊天总会动不动就搞个表情包一样,不用太过于细究其中的变因,“搞”的生命力,早就远远甩你前头。
本文来自投稿,不代表展天博客立场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me900.com/458499.html